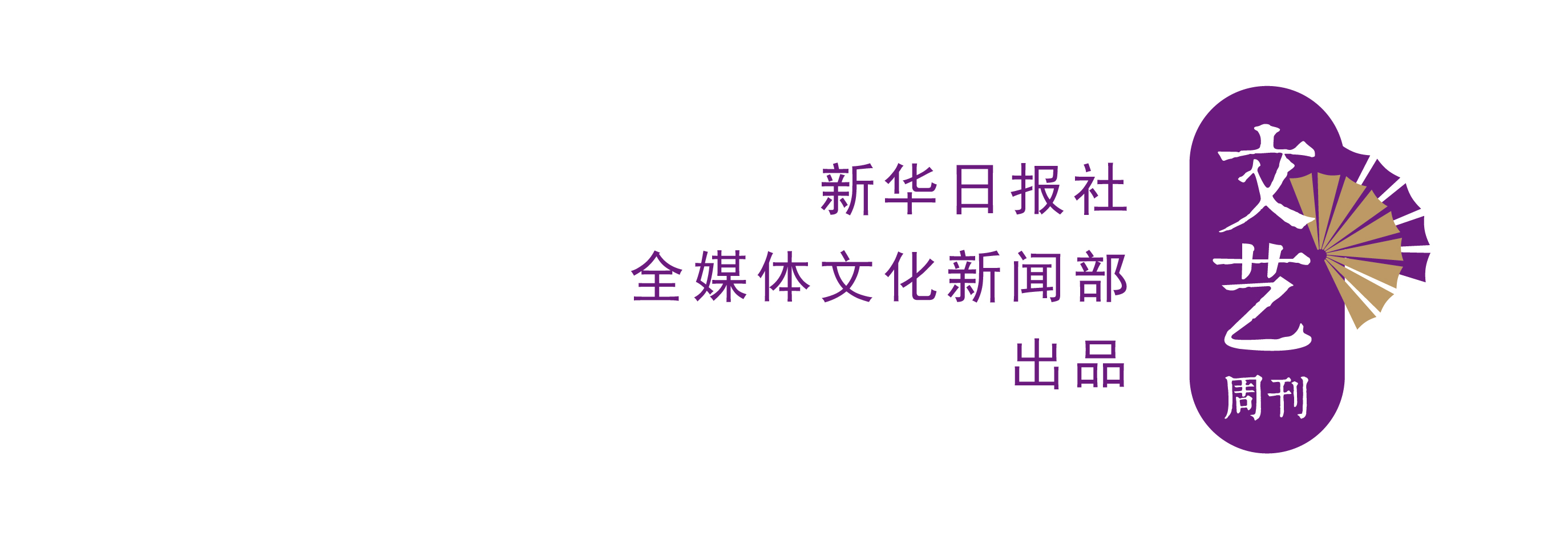6月29日、30日,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创新之作《茶馆》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这位中国戏剧界以先锋、实验、创新而闻名的导演,数十年来坚持不懈为中国戏剧舞台的多元化注入了活力。这次携《茶馆》参演“2019南京戏剧节”,除了《茶馆》本身连演两天之外,孟京辉还参加了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戏剧对谈。对谈结束之后,本报记者对孟京辉进行了专访,请他解析这部《茶馆》的导演视角以及《茶馆》之外的戏剧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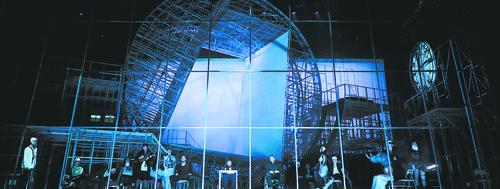
舞台上,巨大的圆形装置传递着时间的错愕,冷峻的灯光照向人类的命运,有人嘶声呐喊,有人奔跑呼号……这是一部与焦菊隐《茶馆》截然不同的版本。时代更迭,命运变迁,人性之思弥漫在舞台上下,潜伏在感性的舞台表象之后的,是直抵人类生存本质的逼问与审视。

6月27日晚现身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张心瑜剧场,与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戏剧对谈的孟京辉,一身黑色衬衣加牛仔裤,秉持他舞台上一贯的简约风格。连日来他的日程很紧张,28日装台,29、30日《茶馆》在南京演出之后,孟京辉和整个剧组将启程前往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作为阿维尼翁的主单元——IN戏剧节73年历史上首部中国大陆剧目入围,孟京辉版的《茶馆》意义非同一般。
三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长、没有中场休息,孟京辉《茶馆》无疑是一次对观演过程的巨大挑战。现场对谈中,吕效平教授对于这部剧给予了高度评价,“孟京辉这一版《茶馆》,大胆把经典拿过来跟当代对话,激活了原作,也用更现代、更哲学的世界观赋予了《茶馆》无限生命力。”
当今戏剧界,“孟京辉”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票房的保证,据说他拥有“刷爆文艺青年朋友圈”的强大能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共创作40余部作品,孟京辉保持着丰沛的创作量,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在刷新自己。今年“南京戏剧节”邀请到孟京辉的五部作品,都是戏迷中呼声很高的热门之作。包括这部去年“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茶馆》、“悲观主义三部曲”中的《琥珀》《恋爱的犀牛》、摇滚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以及“整个剧场笑得人仰马翻”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些都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常常一票难求。去年,《茶馆》在乌镇戏剧节刚刚亮相,4400张票3分钟售罄,曾领跑第六届乌镇戏剧节“最想看榜单”。

大名鼎鼎的《茶馆》,是中国话剧界一座让人高山仰止的山峰。这部老舍先生创作于1956年的作品,以一间“裕泰茶馆”为载体,三教九流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中,展现了历史变迁与人世沉浮。而孟京辉这次要做的,就是“越过山丘”。
这一次,出现在孟京辉舞台上的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人物还是老舍《茶馆》中的核心人物,但是剧情却被天马行空的孟京辉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色彩。经过了他的摔打、揉捏、混合、变形,老舍的《茶馆》不再仅仅是“复制、黏贴”的常规呈现,被催生了全新的自我意识。孟京辉如此解读,“常四爷是头脑和脚,秦二爷是胃,王利发是心,他们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心不一样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可是我觉得‘人’很重要,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熟悉老舍《茶馆》的观众,都知道其经典的三幕时间结构,时间跨越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但在孟京辉的《茶馆》之中,这种线性时间被粉碎和重建了。德国知名戏剧艺术家塞巴斯蒂安凯撒担任这部剧的戏剧构作,他说,今天的《茶馆》像是一场将原始文本与其他文学风格结合起来的实验,自己试图表现的是“一场关于老舍、裕泰茶馆、场馆掌柜王利发和众多形色各异的主顾的时间之旅。”
“在舞台上,你们会看见巨大的一个环形装置。实际上,这部剧的整个时间表达也是环形的。”吕效平解读了舞台装置的象征意味:在这样一个环形的一天天重复的偶然的世界里面,我们才会真正地发现人类的悲剧。

“勇气”和“想象力”是孟京辉在现场多次提到的词。实际上,每一次对经典的阐释、改动或者解构,都会引发一系列衍生的不同声音。围绕着话剧《茶馆》对原著的再创造,吕效平将这种挑战视为一种可贵的艺术激情,“如果没有孟京辉以及孟京辉以后一系列的人来挑战《茶馆》,《茶馆》的经典性将会终结。”

当代实验戏剧作品常常以作者意图为中心,这种自我意图与大众票房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戏剧张力。坚持做实验戏剧的孟京辉,却在商业戏剧之路上走得很顺利。“我们不做金钱的奴隶。”在对谈现场,当被问到怎么看待自己的票房火爆时,他坦率直言,“我们那批80年代的大学生,当说到商业的时候,都带有某种羞耻的色彩。”
但或许恰恰正是这种与观众、市场、注意力刻意保持的距离,让他能留有一些自己的空隙,保持着艺术的独特敏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语言。他说,自己学会了迅速把关注力转化成票房,然后把票房变成对自由自在玩戏剧的支持。 对此,他既感激又感慨,“我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毕业了以后,能像我这样一直做戏剧、能做自己愿意做的戏剧的人,不多。”
观众的需求和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能合在一起,是一种美好的创作状态。“中国当代经历了戏剧漫长的发展历程,从最早的爱美剧、抗战戏剧,到解放以后的样板戏、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戏剧,而我自己正好赶上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实验戏剧的兴起。”孟京辉说,“那时候,观众内心涌动着内在的需求,突然出现了先锋、前卫、实验的东西,它们很新鲜,迅速吸引了一批观众,同时又跟观众一起成长,这些观众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小环境,这个环境是支持我们票房的一部分。”
至于当代戏剧的艺术与票房,作者与观众的关系,在孟京辉那儿就很潇洒地迎刃而解了。“如果有人来质问艺术家,说你怎么不照顾你的观众呢?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真没法找观众。”
古希腊时代,戏剧被认为是浸润与教化的最佳手段,孟京辉却更愿意用诗意的态度来与阐释戏剧与人生的关系:“看戏多美好啊!你看完戏,可以和人聊聊这部剧,戏剧可以进入你的人生记忆。你还可以留下节目单什么的作为纪念。你老了的时候,在病床上已经哆哆嗦嗦说不话来了,你的孙女拿个节目单给你一看,一下就精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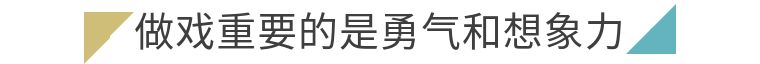
孟京辉说,看戏是对观众有要求的。
“有一次《恋爱的犀牛》的演出现场,两个观众因为占座问题打起来了,周围观众还有人起哄,演出于是暂停了。舞台上,男主演拉着女演员说,一旦观众冲上台来,咱们所有人就跑啊。”绘声绘声地讲罢这个段子,孟京辉笑了,他觉得这一幕就“很有戏剧性”。

实际上,他很关注这个社会的审美教育,这与戏剧的生存其实息息相关。孟京辉说,目前来看戏的观众,可以分为有一定要求的和没有一定要求的。 “戏剧观众得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和审美取向,另外他的成长环境也特别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一个期盼?如果这些都具备了,那就挺好的。”
你认为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这是导演时常被问到的问题。对此,孟京辉的笑容里掩藏不住得意,“其实我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既幽默又不失体统: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下一部作品。或者谦虚点说,都是最好的,都是我的孩子。”
“先锋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对自我的限制,同时也是对自我的煽动。是不是一直先锋下去,这个问题不存在。对我来讲,做戏最重要的是勇气和想象力,剩下就是一些个人质感。”孟京辉其实倒不在意“先锋”这个标签,他喜欢直抵艺术真相。
《恋爱的犀牛》演了20年,已经是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在风靡。“毫无疑问,《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的语言对当代人内心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通过时间的长河慢慢地展示了它的能量。”这个能量之强大,让孟京辉自己都有点始料未及。“实际上我不喜欢已有的这个状况。‘犀牛’已经笼罩了无数的光环,但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没有一版‘犀牛’是我特别满意的,没有达到特别迷人的高度。 ”
十几年前,有大学生排过一版《恋爱的犀牛》,他的做法是让两个马路(剧中男主角)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把马路的台词分成了一个特别昂扬的和一个特别低落的人,最后马路杀死犀牛,实际上就是杀死另外一个不够昂扬的自己。这种创新就让孟京辉觉得挺有创意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版更好的。”
在孟京辉看来,《恋爱的犀牛》所取得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戏剧。“需要戏剧留存我们的记忆,需要戏剧打开我们的勇气,需要戏剧让我们跟世界建立一种友谊和一种和解。否则的话,有可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戏剧是一项人类自我的观照,我一直照着戏剧这面镜子往前走。”
他的戏剧生命力让人惊讶,为中国戏剧舞台贡献的内容和形式也已经足够丰富。他说,自己作为中国当代戏剧舞台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折腾、碰撞,很享受在潮起潮涌中自己的思想变化,“而且我也密切地观察自我的变化,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更加坚强,更有信心往前走。”

记者:您即将率剧组前往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茶馆》作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入选的首部中国大陆剧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孟京辉:对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一起做戏剧的朋友、主创,以及周围这些做当代戏剧的工作者来说,是肯定和褒奖。阿维尼翁戏剧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戏剧节,我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对时代、社会以及生存在这个大地上的人们的看法。同时,它能够向世界展示老舍先生作品巨大的文学与思想魅力。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那里,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当代语言来和世界戏剧同行进行交流,也传播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总之挺好的,挺激动的,也挺高兴、挺自豪的。
记者:一开始,你能估计到对《茶馆》进行再创作之后,会遇到各种声音吗?
孟京辉: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的创作毕竟是对原作品一种延伸式的演绎。我们演完了以后,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老师对我们进行了充分肯定。她说我们首先是爱老舍的,这特别让我们高兴,也鼓励了我们。我想说,我们面对老舍先生,其实是在深情地和老舍精神进行对话,然后把老舍这口井里的丰富宝藏挖掘、呈现出来,同时又不是一种拘泥于原作的简单改编。
记者:改编经典是一件危险的事,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件事?
孟京辉:因为老舍先生《茶馆》剧作本身很伟大,包含着社会性、思想性、批判性,以及对人的悲悯。这是一部很短的作品,但是当你进入到里面,你会发现每一句话都那么有能量。每个在舞台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痕迹,都令你浮想联翩。剧中体现出的中国历史的流变、现象、发展、结局,都让你深有所悟,这样就形成一种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当你面对这么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除了诚惶诚恐之外,还要有勇气,要认真和老舍先生进行对话。
记者:对于经典作品,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可以更好让我们致敬和阐释它?
孟京辉:我们对待人类文化的经典,其实应该站在一个更高远的角度。莎士比亚、契诃夫、贝克特、布莱希特,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有巨大的能量。对我们创作者来说,跟这些经典面对面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特别崇敬的心情。另外,你要有一个真实的反应,要勇敢地把这种反应跟思索表达出来,这个特别重要。面对经典其实更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
记者:能否简单概括一下这部《茶馆》的看点?
孟京辉:我们创造的这部新《茶馆》,从思想上秉承了老舍对人的悲悯态度,秉承了对人物的热爱,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特别传统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坚决不拒绝当代的表述语汇,比如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年轻化的表达,像饶舌歌手出现在舞台上。我们还用了一些新方式来解读人物,比如原来剧中的两个人物变成由一个人扮演,我们还把老舍先生其他的作品像《月牙儿》拉回来,进行一些比照,让这里面能产生一种特别的叠加效果。包括舞台美术视觉上,我们也没有放过,想通过现场建立起跟观众的一种联络和对话。
记者:如果对原作进行了太多实验改编,您担心观众的接受度吗?
孟京辉:没关系,既然创作人员对《茶馆》进行了这么深情的解读,观众最恰当的一个方法,就是上我们这条船,跟随我们去航行。在大海里,沉浸在老舍先生的文学积淀和思想启迪之中,你可以看到更多东西,碰到一些美丽的风景。我其实更希望观众在这个美丽的风景里边迷失一下自己,然后再找回自己。这种艺术化的过程特别美,同时也是真正对经典的尊重和发扬光大。
记者:看到你说自己很喜欢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能被好好讲述的故事都不是好故事”,怎么理解这句话?
孟京辉:就像《罗生门》一样,故事隐藏着巨大的延展性和神秘感,实际上是你对这个世界一种新的认知。故事映射着我们的生存,我们有认知局限,所以讲述它是很难的。同时,我认为对故事的迷恋,不应该是舞台上最终的实践意义,我们应该要找到故事之外的东西,比如情绪、情感逻辑、美学、形式感,甚至一些无法感知、但是我们又必须能感知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从舞台上面弥漫下来,观众在这样的状态下观剧是需要冒险的,但却是一个迷人的冒险。
记者:看得出来,您试图在戏剧之中寄托很多哲学性的思考,这种哲学思考你觉得很重要的吗?
孟京辉:你说的对,其实哲学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离我们并不远。你读叔本华、罗素的著作,其实很浅显,并没有那么深刻,但它是一种思考,是对日常生活的认知。这个认知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甚至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剧组的演员、音乐创作者、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才能一起搭一个房子,不能光我一个人搭。
记者:你曾经发起并担任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等多个重大戏剧节盛会的艺术总监,怎么看待“戏剧节”这个概念?戏剧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孟京辉:“戏剧节”其实就是庙会,有是“酒神”式的美学精神的体现。在中国,我觉着大家凑在一起来做戏剧这件事,觉得真的挺好,大家一起在戏剧中来探讨跟生活相关的油盐酱醋这种小破事儿。只要所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在乐趣当中能产生出能量,在能量里面边把自尊和自信释放出来,我觉得就不白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好多东西是悲哀的,但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悲哀,我觉得从我们的现实意义上来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行走在这种欢乐之中。
记者:通过与世界同行的这些交流,您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国际化有怎样的想法?
孟京辉:我们与国外戏剧其实就是说法方式的不同。跟西方相比,中国戏曲还是很丰满的,而且源远流长。但是这个时代,就像穿衣服一样,T恤、牛仔裤、球鞋,有一种同行的穿衣方式。大家现在做戏剧,我们要提倡“共同方式、独自特点”。首先要回到大家能说同样的话,这样才有得聊,才有意思。
交汇点记者 顾星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