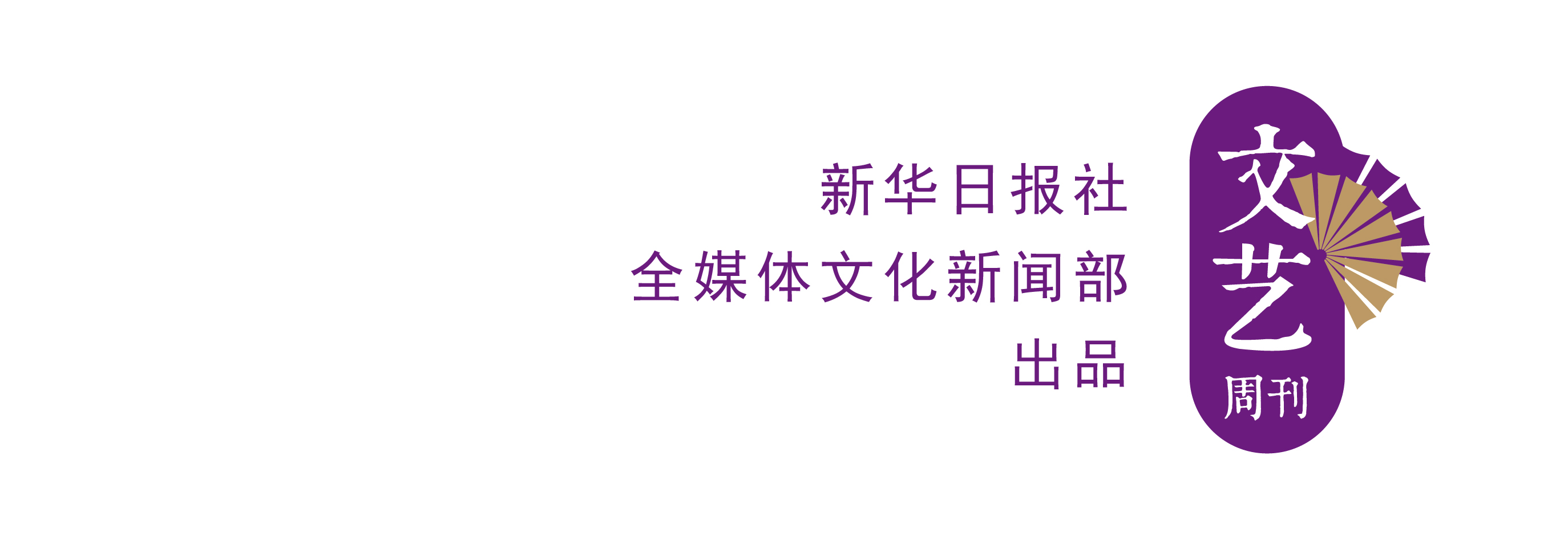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211期)
【繁花】

【新潮】


【繁花】
我们为什么需要小剧场
文/陈捷
小剧场对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城市而言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如果说大型剧院是文化动脉的话,小剧场就是文化生活中的毛细血管。小剧场不仅是演出区域,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江苏小剧场近两年的长足发展,和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小剧场建设从硬件到软件,从理念到实践的顶层设计以及大力扶持有着莫大关联。通过设立剧本创作孵化中心、举办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评选小剧场精品剧场和剧目、承办全国小剧场优秀剧目展演等一系列举措,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自1989年南京举办全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以来,江苏小剧场的又一次蓬勃繁荣、引领全国的新局面。如今,距离这场戏剧节已有34年,距离中国小剧场的发端也已过去41年,一场小剧场运动又在南京声势浩大地蔓延开来。

3月15日,第二届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正式拉开帷幕,20场原创小剧场剧目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南京11个小剧场轮番竞演。4月2日,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也将在南京启幕。在此之前,依托“金陵小剧场展示季”的平台,南京梳理出了107个形态各异,可供多样化、常态化演出的小剧场,城市小剧场集群的概念也从萌芽发展到初具雏形。这一切就像遥远的回声,呼应着34年前的那场“南京戏剧保卫战”。而在理论层面,小剧场戏剧由于成本低,风险小,空间需求和演出方式灵活而可能蕴含的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它与城市生活的密切关联,对于城市空间的精神重塑,以及作为文化消费引擎可能释放的文化新动能,在江苏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我们需要怎样的小剧场?
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在创立之初曾有过一个设想,即一种公益性、艺术性、商业性兼具的小剧场培育模式是否可能?公益性易于理解,强调的是社会效益,使小剧场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而艺术性和商业性则似乎是小剧场的一对天然矛盾。
导演林兆华曾说,中国的小剧场任务有三:一是小剧场形式有利于戏剧的普及,小剧场发挥了戏剧的本质,即密切活人之间的交流的特点;二是小剧场可以给戏剧家提供实验的阵地,不像大剧场那样费钱;三是小剧场可以多改编经典名著,对经典作全新的处理,包括中国传统戏曲。林兆华作为小剧场的发起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这三点中国小剧场的任务对今天小剧场的功能定位依然极具启示。

因此,在小剧场的艺术判断与商业运营之间,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均衡点,即不以票房论成败,不以先锋论英雄,重在戏剧文化的普及和对青年人才的挖掘培养。我们需要的小剧场,是既不被资本裹挟,被当作摇钱树,一味去媚俗讨好观众,也不是将先锋贴上艺术标签。在去年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展演的11部剧目中,既有红色题材、都市情感,也有文学改编和传统戏曲的当代表达。而今年即将上演的20部小剧场作品,题材形式依然多元,除了在高校校园内的三场演出,其余全部公开售票。这算是近年来江苏原创小剧场戏剧为数不多的商业性尝试,但又并非为了商业性。在政府扶持小剧场政策的保护下,年轻的创作者们目前并无票房压力,但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无疑可以提升小剧场在运营上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
而更重要的是,此次小剧场展演,不仅是商演,更是竞演,那么对于小剧场的艺术性而言,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究竟为何?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最关键是原创力。原创性是小剧场的生命力,其规律就是要不断去寻找新的东西,而小剧场的新,关键就在于对演剧空间和观演关系的探索。从《绝对信号》开始,几乎每一部经典的小剧场戏剧都是一次对观演空间的重新建构。在2021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展演中,越剧《金粉世家》、话剧《李叔同》《故障白日梦》以沉浸式演出、延展式舞台、重置观演关系等方式获得了“具有原创性”的口碑和好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文本不足,导演先行,或把“小剧场”理解成只是“剧场小”而已。而一些作品原创力不足,一方面是艺术创造力不够,另一方面其实是创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的思考缺乏深度、广度和高度。小剧场的艺术性最终其实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力。

我们如何建设小剧场?
小剧场建设不仅是基建,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态的系统构建。它应该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物理空间,是剧场建设;其次是空间呈现之物,即内容建设,如何生产原创精品;而更重要的,是空间中的人,是人才建设,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才梯队的培养机制。
近年来,在小剧场空间建设上,江苏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根据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旅厅共同出台的《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小剧场建设评价标准》,全省目前有接近1200个小剧场的建设发展目标。
在内容和人才建设上,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经过两年多的落地实践,已初步摸索出一种将内容生产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模式,一种从剧本到剧目、从文本到舞台、从学校到市场,将创作生产和包括编、导、演在内的戏剧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方法,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两年来中心共孵化原创剧本69部,原创剧目24部,主创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

但从人才培养的梯队性、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上看,小剧场的人才建设目前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建设一个依托戏剧专业大学生的青年实验剧团,面向青年观众,追求当代审美,这可能是小剧场人才培养中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要路径。
当然,小剧场最终的成果,绝不是一个个数字和奖项,而应是一场城市精神的重塑和革新,如金山的那句名言:“戏剧就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艺术”,只有当一个城市的人的活力被激发点燃,这个城市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江苏小剧场今天的繁荣,有外部推动的原因,但还应该是一场内省式的革命,如董健教授将41年前的那场中国小剧场运动称之为一场“悄悄的革命”,“它来自于戏剧内部的要求”,惟其如此,“它才是有生命力的”。

眼下,从每一个小剧场艺术节上传来的讯息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我们更需要一种沉下心来,埋头做戏的“悄悄的革命”。关于小剧场的未来,从理论到实践,我们仍然有很多疑问,小剧场的原创力和思想力如何才能激发?小剧场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真的能平衡吗?小剧场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该如何构建?但我们相信,去做,就会有答案。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教授、院长,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执行主任)

【新潮】
秋白
文/杨际岚
“香港作家闽西行”的日程表上,这一天安排参观“瞿秋白烈士牺牲地”。
到长汀,瞻仰瞿秋白死难遗址,自是题中之义。我至今记得,上中学时,第一次读到瞿著《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大吃一惊:二十岁出头便能端出这般大部头!之后,得知鲁迅先生录清诗人何瓦琴联句,手书条幅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更是肃然起敬!
当年白色恐怖之下,瞿秋白频频遇险,鲁迅曾四次接纳瞿夫妇度过困厄。据许广平描述,“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1934年初,瞿秋白赴苏区,临行话别,鲁迅坚持让瞿夫妇睡在床上,他和许广平睡在地板上。生死之交,情同手足,不能不令人动容。
瞿秋白在长汀从关押到牺牲地有三处:汀州试院囚禁处,中山公园八角亭,罗汉岭下遇害处。和香港作家访问团朋友到了汀州试院。此地宋代为汀州禁军署地,元代为汀州卫署址,明清辟为试院,汀属八县八邑科举应试秀才的场所,后来成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36师师部驻扎于此。院内矗立唐代双柏,已有1200多年,沧海桑田,它目睹了客家首府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一代英杰的生生死死。囚室外,百年石榴依然茂盛。1935年5月9日至6月18日,瞿秋白在狭仄阴暗的囚室里度过了人生旅程中的最后的41天,正是石榴花开的时节。那一年,窗外石榴树应如常绽枝吐蕊,它为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一壮行色。
后人力图还原瞿秋白牺牲时的场景——晴天,餐后,泡上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全唐诗》,集句而成: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书写至此,来人传令催促动身。瞿秋白于是疾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瞿秋白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来到中山公园八角亭。他背着双手,昂首直立,留影告别。当地记者报道:“全园为之寂静,乌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顾盼自如,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他走了二里多,到了罗汉岭下蛇王宫侧,在一处草坪盘膝而坐,平静地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关于瞿秋白就义的资料,基本情况大致相似,亦有细微的差异。比如被枪杀前说“此地甚好”,也有“此地正好”“此地真好”,或“此地很好”“此地也好”。所说的,无论哪一种,似乎都能契合瞿的心境和气概。刑场上的瞿秋白,定格于视死如归。自此,烈士英名远扬,功绩被传颂,精神被讴歌。
曾在微博上读到丰子恺的一段论述,他把人生比作一幢三层楼的房子,“第一层是物质的,第二层是精神的,第三层是灵魂的,世间大多数人住在第一层,一辈子忙于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少数人如学者艺术家等,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即专心学术文化,更有少数人对第二层楼还不满足,爬上三层楼去探求人生的究竟。”我回了一段:“丰子恺之妙喻。上第三层,太少,太难,太险。”
在瞿秋白的临终遗言中,他毫无保留地解剖自己,“探求人生的究竟”,笔者以为这确乎“太少,太难,太险”。如戟又如玉的文人秋白!
而今重读,那些话语似乎仍萦绕心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世界美丽如斯,他于心底再一次地呼唤:“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从汀州试院,到中山公园,再到罗汉岭,瞿秋白走了四十多分钟,他就这样走到了人生尽头。
许广平回忆,获悉瞿秋白罹难,鲁迅悲痛不已。他木然枯坐,挥笔写下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鲁迅强撑着,抱病编辑出版瞿秋白译作,命名为《海上述林》,甚至亲撰广告词,“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高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呕心沥血,为瞿留存最后的纪念。弥留之际,心心念念的仍是亡友的遗著。斯世“同怀视之”的知己呵!
流年似水。诚如遗诗:“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如今,瞿秋白遇难处建起了纪念碑和纪念馆。“闽西行”拟定行程有此一站。香港文友说不去了,“秋白落难,不忍直视,情何以堪!”
驱车经过时,我远远望去,久久无语……